当二胎长成家庭的顶梁柱
 2019-07-09 10:45:50
2019-07-09 10:45:50 来源: 澎湃新闻 湃客 作者:云摩
来源: 澎湃新闻 湃客 作者:云摩
1
陈二娃的大名叫陈霞,她上头还有个叫陈丹的姐姐,都是我大姑家的女儿。
陈霞降生在20世纪末,那正是计划生育抓得最严的时代。二胎是罕见的,并通常被半调侃半艳羡地唤作“二娃”。陈霞成了陈二娃,人们也因此忘了她真正的名字。
我们一家子堂兄弟姐妹里面,陈丹、陈霞离我家最近,幼时常在一处玩,所以这对姐妹成为我当时的观察对象:性格是截然不同的,连长相也不相似,姐姐艳丽,妹妹粗笨,站在一起恰如白天鹅与丑小鸭。
不上学的日子,我们满小镇地疯玩。
镇南两里地外有一间造纸厂,我们发现如果偷偷钻过铁门,就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废纸,其中有数不清的小人书、报纸、杂志、故事书,即便偷偷拿走一两本也绝不会有人发现。
有一回,我们照例摸进纸厂,一边躲避工人的眼光,一边翻捡旧书。我则漫无目的地翻着几本从没见过的杂志,忽然瞟到一则趣闻:美国人是极浪费的,常常不等东西用坏就丢,于是常有人在垃圾场捡到完好的家具或小汽车。
汽车也能捡?!我们镇上还只有两辆小汽车呢!这简直突破了当时连五分钱的水果糖都买不起的我的想象力,我忙拿到陈丹和陈霞面前献宝。
陈霞艳羡地咂嘴:“要是我能去美国就好了,什么都不用买,垃圾场里去捡就行。”
陈丹也说:“是啊,真好,美国人真有钱,要是我能去美国,我就也有钱了,随便扔东西。”
若干年后,最终身处异国的人是我。我蓬乱着头发,裹紧风衣穿行在纽约横平竖直的街巷,逢到允许居民丢弃大件垃圾的日子,路边便堆满各式弃置的生活用品,或新或旧。每到这时,我想起陈丹和陈霞。
那个下午,一母同胞的两姐妹坐在高耸如山的废纸堆下,对同一件事生出了截然不同的感慨,那或许不是她们一生分歧的开始,却是我第一次确凿地看见端倪。
2
两姐妹的路从出生开始就大为不同。
陈丹降生在瞩目当中。
奶奶生育了众多叔伯姑姑,陈丹则在我们这一辈中第一个来到世上。我虽没有亲见,却从长辈们一次次的描述中窥见了当时的情形:一家人面含喜色盯着我大姑的肚皮,看着它日渐鼓胀,待饱满到极致,便魔术般幻化出这样一个粉嫩嫩肉团团的小人儿,一片欢欣。祖父亲自起名,爱不释手。陈丹长得也讨喜,肤色白净,柳眉杏眼,那时大姑每次回娘家,弟弟妹妹们都在门口排队等着抱陈丹,人人口袋里藏着糖。
到十年后陈霞出生时,前头已经有了一大把兄姐,老人们早过足了抱孙辈的瘾——连孙子都有四个了呢。叔伯姑姑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小孩。谁还顾得上一个“二娃”?陈霞不过是这个大家庭里毫不起眼的新成员,最大的影响力是令大姑贫寒的家境雪上加霜。
“你啷个就非要生二娃不可呢?——又过得不好。”家里条件最好的三姑,在大姑向她借钱给陈霞交学费的时候,低声地质问了。
大姑尴尬地笑笑,没有答话,三姑也并不追问。
三姑背着她嘀咕:“这个二娃生来有什么用?——长得不好看,成绩还差……”但她最终给了钱。
几年后,陈丹读完初中,走到了义务教育的尽头。我和陈霞在她俩共享的那间低矮的、四面灰土墙糊满报纸的闺房里同她告了别。陈丹提着一只木头箱子,以一种闯荡的姿态离开。
陈丹辗转去了昆明,正赶上九十年代经济腾飞的大潮,做什么都来钱。她先是给人打工,地头渐熟之后便和人联手做起房地产中介,赚足了钱,买房买车。
我后来去过一次她在昆明的家,四室两厅小跃层的房子,整洁明亮。那时陈丹已为人母,是家里说一不二的女主人,而三岁的儿子志明则受到一家人的娇宠,聪明伶俐,体格健壮,两边四个老人轮番伺候衣食,宛如当年的陈丹。
大姑满面笑容地削着芒果,志明在光可鉴人的木地板上奔跑,鞋底敲出一串清澈的吧嗒声,动听悦耳。我想,那间挤了两个人的四面土墙糊着报纸的闺房,对她而言大概是上辈子的事了。
陈霞则留在了四川老家,大姑的原话是:“生了两个,一个出去了,另一个总要留在身边。”
她一样念到初中毕业,然后开始了打工生涯:饭馆、家具店、美甲店、手机店、鱼庄,一样样做过来,只是都没挣到钱。农村改革后,大姑家的生活渐渐好转,新修了三层小楼,位置也离镇上更近,陈霞便还是住在家里,到后来她跟打工认识的男孩子结了婚,生了孩子,他俩还是住在大姑家的二楼。
姑父和大姑对此则十分乐见。
老两口岁数大了,多年操劳在身上留下了印记,病痛一样样找上门: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关节炎。志明渐渐大了,不再需要人时时照料,他们很少再去昆明,只在家中养老。而有女儿女婿在身边陪守,令他俩感觉方便又安心。
2014年底,我忽然接到家里的电话:“美国那边治眼睛的医生,你认识不呢?”
“不认识……怎么了?”
“志明查出来眼睛里长了肿瘤,恶性的,叫什么视网膜母细胞瘤,命怕是保不住。”父亲语气沉重,“陈丹说能不能弄到美国去治,不晓得那边是不是技术好点。”
我悚然一惊,想起志明虎头虎脑在地板上跑动的样子。
我挂了电话,一番查询后,回电给家人,告诉他们赴美医疗的艰难和高昂费用。
陈丹家似乎也并未认真想来美国,最终还是在国内做了手术。据说效果还算理想,志明失去右眼,但保住了性命。
我松一口气,又零星听闻志明的后况。
听说他恢复得一般,脾气却变得很坏。
听说他再不肯好好学习,总旷课打人。
半年后我听说了志明被送回四川老家的消息。
“你陈丹姐姐说,从小娇惯,全家人宠他一个,完全被惯坏了!”母亲转达陈丹姐姐的话。
“现在闹得太厉害,管不住,索性送回老家,父母不在身边,没得依仗,说不定反而老实点。”父亲也补充着说。
“送回老家谁带呢?”
“你大姑和姑父呗。再说陈霞两口子也在家,帮着看管一下,足够了。”
等一等——可是,说娇惯,不也已经娇惯了这么多年了吗?娇惯他的,不正是你们这些父母长辈吗?怎么忽然就说惯坏了?怎么解决的办法是让他离开父母呢?
许多问题涌到我嗓子里,又在沉默中消失,像许多转瞬破碎的可乐气泡。
一年后,陈丹家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。
3
2017年初,姑父一场大病,全身器官忽然衰竭。
陈霞夫妻半夜慌慌张张骑三轮车送去医院,第二天下午,陈丹夫妻也赶到ICU门外,病危通知单已经下来两次。
四个晚辈分成两拨,一拨守着姑父和医生,另一拨跑上跑下缴费拿药,晚上轮班陪床,总算熬到姑父挣出鬼门关。
姑父脱离危险期那天,陈丹夫妻开车回了昆明。生意不能耽误太久,另一方面,小儿子宏明也让人放心不下。陈霞夫妻责无旁贷。
“放心,医药费我绝不会少出的。”陈丹临走时用力拥抱妹妹,“他也是我爸,有啥子我们两姐妹都一起分担!”
年底回家时,奶奶跟我讲起这件事。
“陈丹个没良心的!”她说。
“怎么呢?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不是刚好?”我问。
“出的啥子钱!”奶奶愤愤然,“两姐妹一人一半出的医药费!”
我愕然。
半晌问道:“可是出力到底是陈霞出得多……是不是姐夫不乐意多出?”
“扯!你姐夫还劝她来的,说再多拿十万块,是陈丹自己不肯,说,‘两姐妹,理当平摊,凭什么我要多出钱?’”奶奶气哼哼地答。
“那陈霞他们怎么出得起?本身就没钱,还要照顾老人带小孩,家里还有田地要顾……”
“有啥子办法,借了钱慢慢还吧。”
怪不得这次回家感觉陈霞夫妻更忙了。
团年的时候,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吃饭。
志明已经完全适应在老家的生活了,进出自然熟稔,看不出性格恶劣的样子,只是也不像当年在木地板上撒欢奔跑的那个小男孩。他走过来叫我“姨”,笑得羞涩,聊天时嘴很甜。
我私下问父亲他脾气还很坏吗,父亲也只是说他懒,不爱写作业,成绩很差,像当年的陈霞。
“那他以后怎么办?”我叹着气替他发愁,“身体不好,眼睛少一只,成绩也不好……虽说陈丹姐姐家有钱,可也不能坐吃山空啊。”
“什么钱?有他的份?”母亲冷笑一声,“你还没看明白么,陈丹他们早就放弃他了,说脾气太坏,又不学好,读书不认真,寒了心了。昆明的家业再大,到那一天也全部是小儿子的。”
“什么?”我惊讶到失语,感觉冷气从背后一直往上爬,半天才找回声音,“那志明以后怎么办?”
“怎么办?只有靠自己。志明看着聪明,其实是个傻的,就知道玩,到现在还没醒悟呢。”
我接不出话。
仿佛有什么东西伸进我脑子里,像那场雨,冰冷的,冻结了思维,抽走了全部思绪。我脑子里空白得一个词也没有。
我无意识地转身走开,茫然越过抽烟闲聊的叔伯,越过和志明宏明打闹的侄子侄女,走到厨房去,几个女眷在里面洗碗。
“——就说去年陈哥那场病,多亏家里有两个女儿。要是只有陈丹一个,又在外地,怎么顾得过来?”
“是噻,养儿防老,留一个在身边保险。”
“所以说嘛,还是起码要生两个——一个不得行了,还可以靠另一个噻。你看宏明长得多壮。”
这些声音轻飘飘随着水声扬出来,似乎并不忌讳被谁听见。
“哎,陈二娃。”一片烟雾中我听见有人叫她的“名字”,陈霞却并没有抬头,“国家现在都放开政策了,你不是独生子也可以生二胎,准备啥子时候生啊?”
-END
推荐相关
本站原创文章可转载,但需注明来源于本站,如有违反,追究法律责任;本站转载文章仅代表原作者个人意见,不代表本站观点,若有任何联动责任,本站概不负责。
客户服务热线:021-61090198转8044或400-775-9967 邮箱:editor@shanghaiyanglao.com
本站版权所有:上海新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shanghaiyanglao.com © 2023, All rights reserved. 沪ICP备17055077号-2
工信部网站链接:http://www.miitbeian.gov.cn/state/outPortal/loginPortal.action
手机上海养老网


扫一扫
我要留言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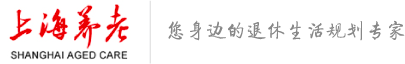

 收藏(0)
收藏(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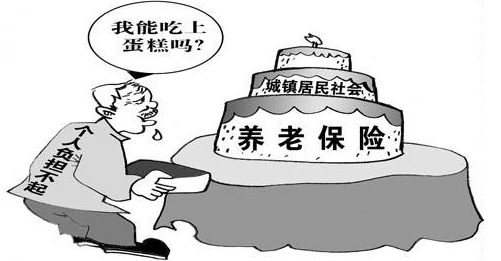


 二维码
二维码 我要留言
我要留言